
作者:王明雅 | 编辑:葛伟炜
“市集是有腔调的,市集人的气息也是相似的。”
城市的年轻人总能找到地方安放灵魂——放心,不是谈飞盘、骑行和陆冲。现在,北京的隆福寺,上海的思南公馆,亦或杭州的湖滨银泰in77,那些知名的艺术街区和商业地产,正热衷于辟出大片空地,支摊聚人。
是市集,它又火了。
市集当然不算新鲜——起码对于刘洋来说。十多年前,他在北京卖二手相机,没开自己的实体店前,就常参加复古市集,和很多有趣的朋友一起,在教堂,在黑楼。他是SpringCameras的创办人,一家曾藏在胡同里、以宝丽来闻名的小店。
市集的概念不必赘述,它历史悠久,不分国界。今天的年轻人更熟悉一种文化性质的新市集,大型活动里,上百个小摊儿呈“川”字型排开,文创、手作、饰品与古着占了主流,如果你注意到的话,咖啡与精酿,也涌入了其中。
偌大的城市里,文青或潮人们曾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市集场所,譬如酒吧和地下车库。但更主流的地方,还是艺术街区,在北京,像798和朗园。现在,商业地产对流量更为敏锐,于是,市集也在购物中心的大门前和大堂中落地生根。
市集是有腔调的,市集人的气息也是相似的。
刘洋称自己是市集的“吉普赛人”,驱车前往各个城市“摆摊儿”几乎已经成为常态,当然,收入之外,更重要的,是去维系旧的友情,收获新的朋友,感受不同的生活。

他不是孤例。以独立设计师和手作人为代表的“市集土著”,同样会将其视为一个社交场所,发现受众和同好,除此之外,完成自有品牌的露出、传播与建设。
很难否认,市集曾经小众,如今愈发有大众化的趋势。遗憾的是,和很多事物一样,日趋大众化的过程,意味着打破原有的结界。“腔调”被稀释,良莠不齐的元素趁虚而入。
当下的摊主与顾客中,也会偶尔冒出“韭菜”的挣扎声,不合格的主办方、参差不齐的商品,愈发昂贵的进入门槛,也在不断为市集祛魅。
行业美好,还很脆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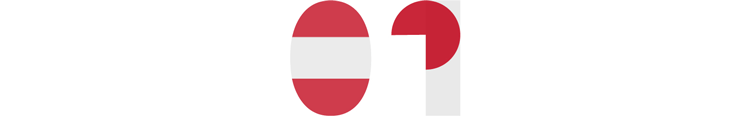
YOUNG形容自己第一次出摊,“手忙脚乱”。垫布是从家里随手扯下来的窗帘,展示道具是平时用的收纳筐,东西直接装进行李箱,当天和朋友一起抬过去。
那是去年中秋节。初衷只是想把家里做出来的一堆东西“销销货”,YOUNG报名参加了多抓鱼的市集活动,并顺利入选。她是一名平面设计师,打理着自己的原创设计品牌“FFclub花野俱乐部”。
品牌原本以售卖原创家居生活产品为主,考虑到多抓鱼的用户调性,应当普遍喜欢读书,她临时让合作印厂切了许多书签状空白卡纸,现场边画边卖,效果很好。
YOUNG运气不错,第一次就感受到了乐趣。
那是一场完全“摆摊儿”化的活动,展位随意铺在地上,无拘无束,YOUNG领到一只小马扎,坐在摊前,像个真正的集市摊主,仰头才能看清顾客。人流量很大,据说进场排队需要两小时,北京的初秋天气干爽,里面却热得人直淌汗,兴许是兴奋。
一个朋友帮忙搬来了东西,还有两个朋友听闻这件事,嚷嚷着过来加入吆喝队伍,“他们纯粹是想来玩儿”。YOUNG同样没忍住诱惑,一天下来,进账1000多块钱,逛别人的摊位又花出去不少。
几年前,从公司出来后,YOUNG运作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,主业还是做商业设计。她感谢花野,作为一名艺术创意类工作者,需要在生存技能之外,找到自我意识和表达的抒发口,花野承担了这样的使命。

市集显然能让花野获得快速的成长。她喜欢这种形式的直接,在一个主流社交与沟通几乎全面线上化的时代,与顾客面对面,意味着更有效、更即时的反馈。
起步中的独立设计师品牌,都需要这样的渠道和土壤。
何溢漾,“像河一样”植物染工作室主理人,主营以草木染布包为主的手工艺品。2019年,因为参加淘宝造物节活动,被不少北京本土市集主办方发掘,邀请参加线下活动。
新产品开发后,溢漾会第一时间拿进市集,感受顾客态度,测试受欢迎程度,灵活调整产品。
她原本有自己的实体店铺和线上网店。
从西班牙留学回国后,溢漾相继在电视台和扶贫基金会工作,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,在北京的北三环安贞桥一带租了门面,售卖自己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小玩意儿。期间,她结识了自己扎染入门的师傅,开始对草木染着迷。

这间小店前后维系了两年。因为市政工程改造,小店关停,溢漾顺势成立了工作室,专心做草木染,同时将重心移到线上,也是因为早期淘宝店铺的高流量而被官方看到,继而邀请参加造物节。
眼下,线上经营困难,疫情下的实体店难开,去年以来,开通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之外,她开始频繁参加市集,希望打开新客户群。好在结果不错,溢漾粗算了一下,目前市集的销量占比已经达到60%~70%。
“市集也是后疫情时代下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形式。”她总结。在没有实体店的情况下,职业手作人大概率需要网络营销,但面临周期长的难题,相比较而言,“市集是最快、也是比较好的展现方式了”。

成立于2015年的伍德吃托克,几乎已经成长为市集业态的标杆,年均20场活动,涵盖文创、美食、生活方式等各类内容,紧追潮流,并创造潮流。
伍德吃托克有壁垒,它对新锐品牌和独立设计师品牌有极强的吸引力——基于自身的策划、宣发能力和日积月累的口碑。创作者们知道,来这里,不缺流量。
显然,并不是每一个市集都能成为伍德吃托克,特殊的疫情时期,市集早已超越了“对话年轻人”的职能,成为一种赋能手段。

2020年,中国商业研究院发布一份《上海集市白皮书》,其中提到,要将上海打造成“全球集市的标杆”。其中,安义夜巷、大学路游园会和思南夜派对等多个集市项目,经改造后,人流量较之前普遍提升超50%,商铺营业额也有显著改善。
商业地产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。有相关数据统计,2020年,单商场空间就举办了超1000场市集相关主题活动。
何溢漾明显觉得,市集发展太快,导致质量参差不齐,需要好好辨别。YOUNG有过经验教训,绝不参加商场活动,因为限制多、耗时长——摊主必须要在商场开门前到位,一同结束营业,既费精力又费时间。
不久前,“清风和烈酒er”在小红书发出“怒吼”:“现在的市集就是变相的主办方割韭菜。”这则笔记火了,有相似感受的摊主在评论区聚集,分享糟心事。
清风做手工饰品,售卖成品珍珠和水晶,有同名网店。她不是职业摊主,做工程造价,供职于深圳一家房企。因为对手工和饰品的喜爱,才慢慢将其发展成副业。她开玩笑,“房企的现状嘛,你知道,有个第二职业也不错”。
清风解释,市集报名通常是“打包”的形式,5~10天不等,多的甚至达22天,即连续出摊天数,工作日也不歇息。在深圳,摊位费至少200元一天起步,越靠近市中心越贵,但人人都知道,工作日几乎没有人。
何以为“韭菜”?
商业地产或文化街区们并不直接招揽摊主,需要“中介性质”的平台帮助策划招募,也就是摊主们常说的“主办方”。市集火热,不少小型主办方趁势崛起,又因自身策划能力不足等原因,导致活动体验不佳。
清风常碰到的情况是,一场市集20余摊位,一大半都做饰品,只能打价格战。她明显打不过,即便已经熟练,一件作品从构思到制作至少需要一个小时,而不少职业摊主直接从1688等批发平台进货。普通人很难有耐心去仔细分辨,为手工付费,更是奢侈。

圈子内,因为实际人流量与预期严重不相符,导致摊主维权退钱的事件并不少见,但退钱仅能挽回部分损失,摊主们付出的人力、时间和交通等成本,覆水难收。
清风参加市集的时间并不长,如今也能明显察觉到,一件正常事物运行偏离轨道的错位感。单这半年,深圳关外的小商场市集,摊位费就从180元/日涨到200元/日,5月份,这个价格可以参加市里更好商圈的市集。
清风猜测,行情不好,许多人把创业当成避风港,出摊去市集最便捷,导致一些原本知名度不高的市集,摊主报名也竞争激烈,费用旋即水涨船高。
花钱的消费者当然也会成为“韭菜”。
以伍德吃托克为代表的知名市集活动,花钱购买门票入内,已经成为默认的规则,本质上,那里更像同好集聚的“社群”,发现前沿事物的通道,溢价有用。
尤其以驻扎商场的市集为甚,越来越多纯消费向的活动,也开始兜售门票,数额不等。在小红书,不少人抱怨这样的市集活动,“明明是来消费的,花钱才能进”,仿佛大冤种。
有趣还好,最怕“货不对板”,花钱进入,发现“图文不符”。
回过头来看这场起于2020年的市集回潮,市集人带着梦想与爱好涌入,显然是其中难得一见的精彩因子。疫情的作用下,市集已然在短期被催熟——城市需要活力,年轻人需要去处,空间需要人气。
小众事物终于被放大,被消解了“腔调”。

2020年,刘洋才正式成为市集“吉普赛人”。他搬到了天津。
SpringCameras第一家店在北京鼓楼附近的胡同里,2012年开业,几乎是北京最早的宝丽来主题店,并很快成为那时候知名的文青打卡点,后来,因为各种原因,店铺搬到了一处商务楼里,不好找。用刘洋的话说,“进去很麻烦”。

它的北京时代终于还是结束了。2020年,因为实体经营困难,天津的房子又已经交付、拾掇好,刘洋和妻子、孩子一起离开,定居天津。SpringCameras重回线上经营,主要交由妻子打理,他则回到了市集。
他开车出去。市集能帮忙再拓展一点新客户,运气好的时候,参加一天收入几千元能回本,差一点的时候,他纯当去旅游。之前去成都,他还去本地拆迁的飞楼里逛了逛,捡了些被原主人留下的东西,如花盆和旧桌椅,他喜欢这些。
去年三月,他去杭州参加一场市集活动,重遇了熟人“蝴蝶公主”—— 一位因着装奇异而被外界熟知的亚文化先锋。他们一起吃火锅,进电梯的时候,碰到曾经来店里买相机的顾客,两位男士,现在分别创业做咖啡和服装,于是攒到了一个局。
不久前,他刚参加完朗园的北京图书市集,十月底,会再度启程去杭州的大娃怪市,一个业内知名的古着市集品牌。
市集当然是有价值的。它延续了SpringCameras的生机,成为刘洋与外界连接的纽带。
何溢漾的生活也已经与市集牢牢绑定。
最近三个月,她几乎每周末都会参加一场,白天出完摊,晚上回家继续赶制订单和第二天的货品。手工包需要自己染色、自己缝制,耗时,但她享受其中的过程。
她刚做草木染时,国内普通受众的认知几乎空白,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云南的文旅产品上,因此,出摊总是科普大于售卖。最近几年,草木染被越来越多年轻人看到并加入职业手作人的行列,选择愈发多样化,客户的选择和购买力也相应提升。
溢漾说,她会一直做下去。“不同的时间地点,不同的面料,不同的媒染剂和不同的植物,每一次染色效果都不同,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。”
前段时间,北京一场市集活动上,知名编剧史航从花野的小摊上买走些喜欢的东西,史航捂得严实,但被YOUNG认出来了,她没好意思搭话。回来后很久,才和团队的朋友提起这件事,朋友“恨铁不成钢”:“起码去小红书宣传一下。”
此前,不乏有剧组的服装造型师选中她的衣服,最终在影视作品里出现,她都默默略过。“不是说有名人用了你的东西,你就特别牛了。”

她对花野的期待很佛系,“自负盈亏就好”。
她喜欢市集里的反馈。做了多年设计师,甲方客户满不满意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,但在市集里,喜欢花野的顾客会直白地反馈自己的见解。他们喜欢花野不故作高深,是能看得懂的艺术。
清风喜欢摊主们。
可能是幸运。清风觉得,她遇到的摊主都很好。第一次出摊,三天销售额300块,隔壁做“大炮机”生意的大叔都看不下去,主动过来“在线指导”,她的摊位没有射灯,大叔直接把自己的拿来帮她挂上。同是卖饰品的人,还会传授经验,教她如何摆放更好看。
朋友和同事也永远在第一线呐喊加油。“每次去参加,我的摊位生意没有多火,但一定是最热闹的。”清风笑。
以上,才是市集里最重要的事。
以上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市集?东京爱情故事歌词的全部内容了,希望大家喜欢。